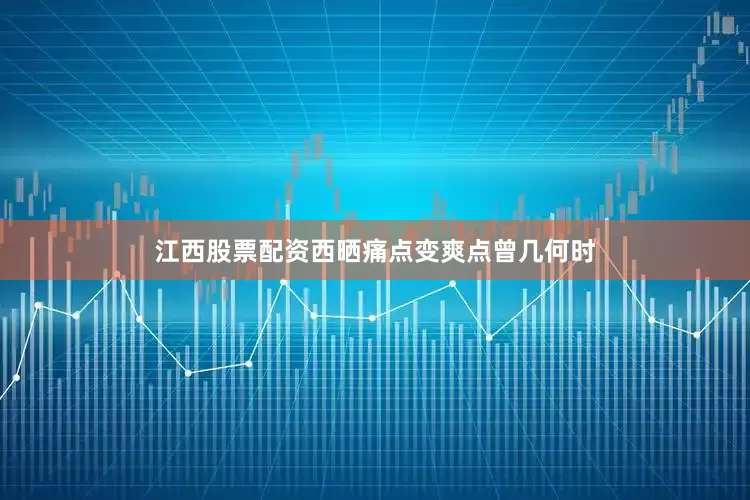后台回复 品牌 免费送你《135本品牌营销必读书》
作者 | Sunnyue 来源 | 首席品牌观察
宗馥莉执掌娃哈哈的这一年,像一场急转直下的雨,把曾经看起来稳固的一切都浇得透湿。
去年7月她以退为进接过权柄时,不少人盼着这个新时代能给老品牌带来新气象。
可一年过去,留在员工心里的只剩寒意。

宗馥莉,还在收拾烂摊子
2024年7月,宗馥莉以退为进接过权柄时,娃哈哈的空气已经变了。
父亲留下的不仅是近800亿营收的盘子,还有层层叠叠的“体外公司”和扯不清的产权。
她的改革来得又快又猛:去年9月起,老员工被批量转签至宏胜系公司,干股分红没了。
“基础工资+奖金+补贴”改成单一年薪,实际收入缩水四成。
陕西工厂待了20年的工人发现,连基本工资都降了70到180块,燃油补贴、房租津贴说没就没。

▶ 图源:中国企业家
没转签的研发人员更无奈,今年每月工资比去年少,半年下来每人少拿六七万,年终奖缩成了个零头。
销售部门的日子更难。
今年6月新考核制度下来,没经过职代会表决,员工不签字就被拦在会场逼着签。
条款苛刻得像故意逼人走:客户经理完不成翻倍任务就降成铺货员,4月一份通报里,224个“累积负增长”的人一夜之间换了身份。
销售人员基本工资2490元,扣完保险只剩几百块,出差没差旅费,驻外没补贴,有人苦笑“现在是贷款上班”。
北方有区域连续三个月业绩下滑50%,业务员开庭日期都定了,还得顶着大太阳去终端店上货。
从少年干到大叔,心里总有点放不下。
7月本该是饮料旺季,别家销售忙着出货,娃哈哈的人却在研究新制度。
全国销售连续三个月负增长,经销商开始躺平,南方市场偶尔持平,也是业务员压货压出来的。
更糟的是6月有基地工厂被曝用过期原料生产双柚汁,市场监管部门上门时,货架上的双柚汁还贴着“新鲜日期”。
北京便利店开始缩减娃哈哈陈列位,有店长说“卖完这波不再进了”。
宗馥莉站在父辈留下的遗产里,一边要应对家族纠纷,一边还要收拾业绩烂摊子。
父亲用三十年证明,造饮料和造人设是两回事。
前者靠渠道、产品和信任,后者靠包装、情绪和默契,而默契这东西,碎起来比玻璃还快。

大器晚成!娃哈哈的崛起之路
1987年的杭州街头,42岁的宗庆后拉着黄鱼车在小学门口穿梭,车斗里装着课本和雪糕。
那时没人能想到,这个中学毕业后去舟山晒过盐、在绍兴茶场种过稻的男人,会用十几年时间造出一个饮料帝国。
他从浙江医科大学一位老师手里买下儿童口服液配方时,大概也没细想。
14万元启动资金以“借款”名义注入区教育局下属校办企业,会为几十年后的产权纠纷埋下伏笔。
1991年秋天,杭州上城区那家叫“校办企业经销部”的小铺子已经装不下了。
宗庆后带着刚破2亿元的营收和4000万利润,盯上了濒临倒闭的杭州罐头厂。
这桩“小鱼吃大鱼”的并购在当时足够大胆。
街道小厂吞并市属国企,在沉闷的经济环境里像一声惊雷。
那时的宗庆后,脸上带着杭州人特有的腼腆,说话时总笑眯眯地抽烟,遇到投缘的人就不停地递烟,聊半天能在对方面前堆起七八根。
这种带着江湖气的实在,后来成了他最厉害的武器。

▶ 图源:微博
1992年南京市场遇挫,当地质检部门刁难,销售经理愤而服毒(后抢救脱险),他在《南京日报》登整版广告宣布退出,引得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文声援。
这场“果奶风波”意外帮他打破了区域壁垒,也让他摸到了舆论的脉搏。
有时候,看似被动的处境反而能变成破局的钥匙。
真正让娃哈哈站稳脚跟的,是1994年推出的“联销体”模式。
每年经销商大会上,他要求客商先交保证金,公司按高于银行利率付息,进货一次结算一次。
这套玩法既解决了欠款难题,又把经销商绑成了利益共同体。
那些年,宗庆后一半时间在路上,跑遍全国帮经销商调货,经销商大会上满是十几年的老面孔,见到年轻的就问“你爸妈是谁”,“娃二代”“娃三代”成了行业奇观。

宗庆后,打造的爱国舆论根基
这个把自己活成“工作机器”的男人,除了办企业几乎没有别的嗜好。
不打高尔夫,不追名车名表,浙商圈子里的论坛和活动很少见他身影。
他把两个关系处得极牢:对员工,几乎不轻易开除人,老员工更被当成家人;
对经销商,很少有人做娃哈哈的生意亏过钱。
至于政府、银行和媒体,他要么懒得应付,要么用最直接的方式。
1996年和达能合资时,他大概没多想,4500万美元加5000万商标转让费换对方51%股权,会在11年后引爆一场风波。
2007年的“达能之争”,第一次撕开了他“民族企业家”人设的口子。
他在舆论场上高喊“让中国人拥有中国品牌”,用民族主义情绪对冲契约争议。
后来的宗庆后,渐渐成了公众熟悉的模样。
穿百来块的布鞋,坐高铁二等座,说自己一年开销只有五万块,强调“不上市、无外籍、不海外置业”。
这些细节像散落的珠子,被舆论串成“首富清流”的项链。

▶ 图源:微博
没人深究娃哈哈1994年就试过上市,没成是因为股权太乱;
也没人细想,为什么“坐二等座”的场景总在特定时刻被拍到。
布鞋本是贫寒出身留下的习惯,却被附会成“富而不骄”的象征,连他自己似乎也默认了这种默契。
公众需要一个道德标杆,他需要一个品牌保护伞,各取所需。
他太懂人们想听什么,就像当年知道家长们爱听“喝了娃哈哈,吃饭就是香”,如今也知道“爱国”两个字能轻易点燃情绪。
只是他没料到,亲手搭起的人设大厦,会在自己身后塌得这么快。
搅得更凶的是香港那场“20亿美元财产案”。
宗庆后同父异母的弟妹突然现身,索要信托资产和近三成股权,若胜诉,宗馥莉的控股地位就得动摇。
更刺眼的是纠纷扯出的资产转移,她想把387件“娃哈哈”商标挪到宏胜系,被杭州国资紧急叫停;
18家跟原告有关的工厂说关就关,22%的产能没了,部分订单只能找今麦郎代工。
经销商队伍也散了:大的抱紧宏胜拿高返点,小的被“竞标制”淘汰,浙江一个做了30年的分销商,最后转投了农夫山泉。

这一切,像极了宗庆后时代埋下的雷。
当年他靠个人权威省去现代治理的麻烦,用“爱国营销”代替品牌建设,把产权藏在层层嵌套的公司背后,以为能把帝国牢牢攥在手里。
可当那双布鞋的神话被遗产纠纷撕碎,“民族企业”的标签成了舆论笑柄,才发现没有制度托底的权威,终究是沙上建塔。
如今的娃哈哈大厦里,老员工怀念宗庆后时代“不轻易开人”的日子,新制度下的销售盼着“换谁来都比现在强”。
*编排 | 三木 审核 | 三木
品牌最新资讯,尽在【首席品牌观察】↓↓↓
行业资讯、案例资料、运营干货,精彩不停


灵菲配资-灵菲配资官网-股票配资是什么-线上配资开户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2024年配资网最新消息公布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及日常生产经营
- 下一篇: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