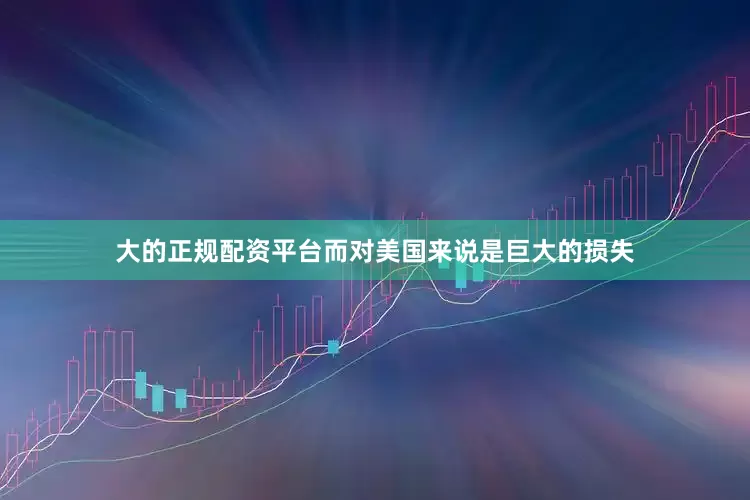人们在生活中或是由于社会原因,或是由于自然原因,实现不了某些愿望,文学给予替代性的满足,使他们疲倦的灵魂得到滋润和养息。
——《弗洛伊德论美文选》
前天,追光新作《聊斋·兰若寺》首映。
故事的主轴很单纯:青年书生蒲松龄行路遇险,不得已夜宿兰若寺,妖风卷起,被一只蛤蟆精、一只乌龟精抓到一口奇异的古井底,见识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异世界。两只精怪比赛讲故事,并逼迫蒲松龄一评高下,稍有不公,裁判便有性命之虞。机智的蒲松龄最后以自己的奇妙故事,一举扭转局势,把蛤蟆乌龟讲得哭成泪妖,得以逃离……
本片采用“一拖五”结构,以《井下故事》穿针引线,由五个聊斋故事改编而来的《崂山道士》《莲花公主》《聂小倩》《画皮》《鲁公女》,组成情节主线。五个故事,画风各异,由孩童世界的烂漫天真,逐渐过渡到人鬼情缘的复杂纠葛。

追光新作《聊斋·兰若寺》海报。兰若,梵语“阿兰若”省称,原指树林、寂静处,后多指寺庙。
受1988版电视剧《聊斋》影响,大家心目中的聊斋宇宙,几乎与“鬼故事大全”画上等号,似乎是炎夏消暑、背后生凉的必备品;蒲松龄本人,在《聊斋》自序中也号称“雅爱搜神,喜人谈鬼”。
但这并不等于说,《聊斋志异》就只是一部鬼怪传奇,这种标签化理解,其实是窄化了这部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作品的丰富内涵——原著共有491个故事,电影此次呈现的五个故事,就恰好呈现了《聊斋》的真实面貌:一座不限于鬼怪故事,蕴藏人性深度、社会关怀与艺术想象的多维宝库。
聊鬼说狐?实谈人性世情
《聊斋志异》,表面上看,记叙了大量鬼狐仙妖的传说,实际上,鬼怪也好,精灵也罢,映照的都是人间百态。
蒲松龄巧妙借助超自然的外壳,在“姑妄言之姑听之”的掩护下,完成了对人性真实而深刻的探索,直面人性的光明与阴暗。

电影中,蛤蟆、乌龟二妖精对蒲松龄死死纠缠
人性善恶的基本判断尺度,在《聊斋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蒲松龄深受儒家思想熏陶,又长期担任私塾教师,将儒家倡导的基本道德理念视为做人的根基,乃至穿越生死,永恒不变。
开篇《考城隍》,便奠定了全书的道德基调:书生宋焘病死,因“仁孝”被选为城隍,又因为老母尚需供养,哭请还阳,九年后,母亲去世,宋焘才回到阴间赴任。而《席方平》中,席方平前往地府,为父伸冤,百折不回的坚韧意志,被蒲松龄赞为“忠孝志定,万劫不移”,表达了对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的英雄气概的敬意。
《聊斋》中,鬼狐花妖幻化而成的女性,往往被赋予超越常人的勇气与智慧,蒲松龄在他的文字王国中,为女性构建了挣脱枷锁、追求自我的可能。
本次《聊斋·兰若寺》的几个单元,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与有意识的加工,就敏锐地捕捉到蒲松龄总的思想基线:无论是莲花公主的娇憨坚韧,聂小倩的柔中带刚,还是鲁公女的豪气爽利,无一不体现出尽力掌控自身命运走向的魅力;就连《画皮》单元,原本隐忍到极致、面目模糊的王生原配陈氏,在故事结束时,也被赋予了新的性格侧面——能够不断被赋予现代化的诠释,恰恰证明了蒲松龄笔下女性形象的蓬勃生命力。

《画皮》单元,王生妻子陈氏对镜神伤
通过鬼狐精怪的媒介,蒲松龄构建了一个可以自由探讨人性的文学空间。在这个空间中,异类往往比人类更富有人情味,而权贵则常常暴露出比妖魔更可怕的兽性。这种角色倒置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讽刺力度,更提供了一种超越世俗成见、直指人性本质的独特视角。
正如郭沫若所评价的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,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,蒲松龄通过鬼狐世界这面魔镜,照出了人性最本真的面貌。
叙事离奇?更为刺贪刺虐
《聊斋志异》绝非仅为满足读者猎奇心理而作的消遣读物,在那些离奇怪诞的情节背后,跳动着一颗炽热的“社会良心”。他以鬼狐故事为载体,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全方位批判,体现了兼济天下的道德勇气与社会责任感。
《席方平》,就是这样的名篇:
席方平的父亲席廉因与富户羊某有仇,羊某死后贿赂阴间差役,使席廉在阳间受折磨而死。席方平决心魂赴阴间为父伸冤。他先到城隍庙告状,但城隍受贿,以“无据”为由驳回;上诉至郡司,结果郡司同样受贿,反将他毒打一顿;继续上诉至阎王,但阎王已被贿赂,对他施以酷刑,企图逼他放弃。席方平坚贞不屈,阎王于是假意答应平反冤案,实则让席方平转世为婴儿。席方平愤而绝食,三日而亡,魂魄继续寻找二郎神伸冤,最终揭露阴司腐败,阎王、郡司、城隍均受严惩,羊某家产被没收,席家得以平反兴旺。
这个故事描绘的阴司,实则是人间官府的镜像,蒲松龄表面控诉的是阴间的贪官污吏,但实际上,何尝不是一卷封建社会整个司法系统的“百丑图”?
更尖锐的则是《促织》,皇室沉迷斗蟋蟀之戏,导致“每责一头,辄倾数家之产”,百姓成名一家,就因这小小蟋蟀,几乎家破人亡。在这一刻,人对待同类之残忍刻毒,已经比鬼怪可怕百倍。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,目睹天灾人祸,对农民\"嗷嗷饿眼生空花\"的困境感同身受。本篇继承的,正是《捕蛇者说》的批判精神。
其他如《红玉》中的宋御史、《向杲》中的豪门公子,多是恃强凌弱、欺男霸女、草菅人命,这些描写都非凭空想象,而是来自对社会现实的长期观察提炼。
作为科举制度下的失意者,蒲松龄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尤为深刻。他19岁便以县、府、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,却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科举路上屡试不第,直到71岁才成为岁贡生。这种切肤之痛,转化为文学创作中的犀利批判。《叶生》中,文章词赋冠绝当时的叶生困于名场,弟子用其文章却能高中;《贾奉雉》中,主人公刻意以拙劣文章应试,反而高中——这些荒诞情节,直指科举制度的非理性,为《儒林外史》先声。
蒲松龄通过《聊斋志异》证明,短篇小说完全可以承载深刻的社会思考。那些看似荒诞的故事,实则是观察社会、批判现实的棱镜,折射出封建体制下的种种不公与扭曲。
万物有灵?老塾师的童心
此次的动画电影,《莲花公主》,是各种选本极少注意的一篇;但以这篇为出发点,探访聊斋宇宙,三全君发现:除了那些揭露社会黑暗、探讨人性深度的严肃作品外,还有大量风格迥异的“咏物之作”——它们往往篇幅短小,想象绮丽,充满童趣,丰富了聊斋世界的光谱。

动画中的蜜蜂王国
也许这跟蒲松龄的长期教师生涯有关——跟孩子的世界贴近,就是容易拥有赤子之心和烂漫诗意的。
基于物性的想象与升华,是这类作品的鲜明特色。蒲松龄具有将平凡事物转化为奇妙艺术形象的天赋,通过拟人化手法,赋予非人类的动物、植物以情感与人格,而且,物性、人性结合,读来妙不可言。
《莲花公主》篇,蒲松龄将蜂巢想象为一个微型王国:窦旭昼寝入梦,被引入“桂府”面见国王,因文采获国王青睐,得以与莲花公主成婚;当王国遭巨蟒侵袭时,他带着莲花公主逃回现实。醒后,有几只蜜蜂围着他起舞求助——邻家蜂房果然被大蛇占据。于是窦旭杀蛇,又为蜂群筑起新巢。
而作者是怎么在梦境之中,暗示“桂府”为蜂巢的呢?“叠阁重楼,万椽相接。曲折而行,觉万户千门,迥非人世……”确实符合蜂巢的物理结构;莲花公主,步态是“凌波微步”,房中是“穷极芳腻”,更兼腰细足小,蒲松龄作为“童话作家”,也是完全合格的。

动画中,莲花公主被改编为十岁左右的孩子,与同是孩童的窦旭结下生死友谊
紧挨着《莲花公主》的,则是《绿衣女》。这一次,是一只绿蜂化为女子与书生相恋,“绿衣长裙,婉妙无比”,“腰细殆不盈掬”的体态,就更符合蜂类特征了;尤其可爱的是,绿衣女用纤细的嗓音唱完歌,围着屋子小心翼翼地转了一圈,生怕有人,纯然是小动物胆怯柔弱的样态。被蜘蛛网缠住,也是蜜蜂经常的遭遇——这个细节,就被《兰若寺》的编剧移入了动画中。
大胆猜测,《聊斋》动画如果还有下一部,这类可爱的咏物小文,一定还会被挖掘改编;而这样的作品,据三全君统计,至少有四十篇。
能够将科学观察与艺术想象完美融合,蒲松龄真是宝藏作者!
蒲松龄的童心,使得他的咏物小品,散发出迥异于鬼怪妖狐、社会关怀类作品的轻松感,像是《小猎犬》中出现的微型猎人队伍,专业杀蚊,还留下了一条只吃蚊子的小猎犬,可知蒲松龄当时必然饱受蚊虫袭扰,遂以想象自我解困;《鼠戏》《蛙曲》,老鼠青蛙各具表演才能,展现作者对小小生灵的浓浓兴趣;而《骂鸭》通过偷鸭者身上长鸭毛的荒诞情节,让物性转移到人身,更是体现出古代作家群体里稀见的幽默感了。
已识乾坤大,尤怜草木青——唯大艺术家,能将平凡点化为传奇。
神性、鬼性、物性、兽性,皆是人性的隐喻。
好的创作者,不仅记录已有,更创造或有;不仅反映确定性,更启示可能性。
来源:中华书局三全本微信公众号
新媒体编辑:宗敏
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
灵菲配资-灵菲配资官网-股票配资是什么-线上配资开户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怎么开通杠杆\n\n老师为学生讲解水稻生长过程
- 下一篇:没有了